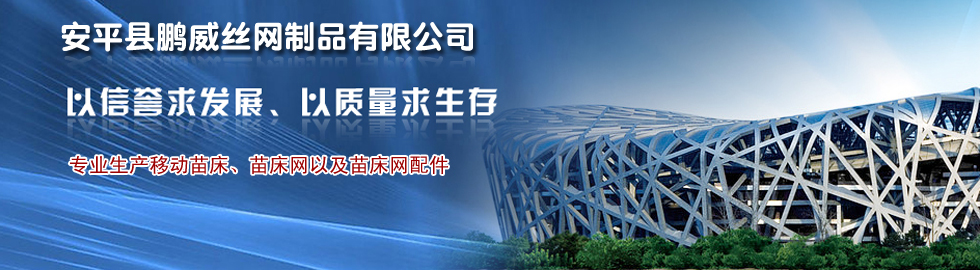
手机:
传真:
邮箱:
地址:
李公明︱一周书记:涂鸦中的反抗欲望与……美国街头政治学
《街头艺术》,[英]西蒙·阿姆斯特朗著,陈梦佳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6月版,200页,59.80元
自从涂鸦和街头艺术诞生之日起,人们一直提出各种问题,例如涂鸦是一种犯罪行为吗?它称得上是艺术吗?它们的创作者通常是什么人?为了什么目的?稍微愿意多思考一下的人还会继续追问:“涂鸦”与“街头艺术”的概念和内涵是什么?在城市文化中,它们具有何种意义和价值?它们的发展与演变过程说明了什么问题?如何从学术的视角来观察和研究街头艺术?从我阅读过的几本涂鸦艺术画册和相关著述来说,英国艺术评论家西蒙·阿姆斯特朗(Simon Armstrong)的《街头艺术》(Street Art,2019)虽然只有十万字左右的篇幅,但却是关于涂鸦和街头艺术的较有系统性的著述,在脉络清晰、简明扼要的叙事中不乏与亚文化相关的艺术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面向的思考。
涂鸦与街头艺术在艺术史主流叙事中难免要被冷落,只有在专门关注西方社会抗议政治的那些艺术著述中,街头艺术的发生背景、视觉意义、传播方式以及抗争遭遇才能得到关注。在利兹·麦奎斯特(Liz McQuiston)的《抗议!——社会与政治抗议的图像史》(Protest!——A Histor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Protest Graph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9)中,涂鸦艺术与版画、漫画、海报、壁画等图像、图形一起表达对西方社会与政治的不满和抗议。不难想象的是,作者当然不是仅仅埋头在图书馆或美术馆展厅,“我参与社会运动已经有多年了,我永远不会放弃”。这是她在网络上的宣言,与那些永远不停止行为的涂鸦写手相似。激进艺术家尼古拉斯·兰伯特(Nicolas Lampert)的《美国人民艺术史:250年的行动主义艺术家和艺术家在社会正义运动中的工作》(A People s Art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250 Years of Activist Art and Artists Working in Social Justice Movements,The New Press,2013)把艺术史与社会政治史紧密结合,在女权主义运动、民权运动、环境运动、反全球化运动、当代反战运动这样的视角中研究愤怒的、抗议的、行动的艺术家及其作品。其中有一章专门论述1988-1989年在纽约发生的以抗议核武器为主题的涂鸦和街头艺术运动,但其论述的视角更多是属于抗议运动的政治性与社会影响。因此,阿姆斯特朗这本《街头艺术》的多方面视角和有深度的论述是很值得阅读的。
“涂鸦”“街头艺术”等概念的词义实际上很难严格界定,尽管作者在这方面都有表述,而且在书后还有一份专门的“术语表”,但是前后各种说法还是难以完全统一。有三个核心概念必须梳理一下,那就是“涂鸦”“涂鸦艺术”和“街头艺术”。在我们的一般认知中它们都比较接近,实际上还是有些区别的。在我读过的相关著述中,阿姆斯特朗在该书中有关这些概念的论述是比较有条理和相对严谨的,而且其中也有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
首先,“‘涂鸦’这个词极其宽泛,用来涵盖墙上的所有绘画,从厕所墙上的乱涂乱画到一整列车厢上被画满图案的列车涂鸦”(10页)。那么,“什么是涂鸦?一个人未经允许在他人的私有物品上进行涂画,这种行为就被称为‘涂鸦’”(12页)。应该说这个定义比较符合我们通常对建筑、交通工具等空间中的“涂鸦”的认知。但是在书后的“术语表”上,“涂鸦”(Getting up)是指“将自己的名字写在墙上的行为。与‘轰炸’的意思一样”(180页)。那么,“轰炸”又是什么意思呢?“轰炸(Bombing):外出的涂鸦活动,目的是尽可能多地覆盖物体的表面。”(同上)很显然,“术语表”解释的是涂鸦文化中的行话、黑话,不是关于概念解释的正式条目。结合涂鸦的发展来说,在墙上写自己的名字就是原始的签名涂鸦,但是后来书写的内容超出了签名。很有意思的是,阿姆斯特朗不仅指出“涂鸦的内容可能是幼稚的笑话、政治抗议,或是某个帮派的标语,也可能是某种签名或者符号”,同时更进一步从出版的自由的角度来阐释“涂鸦”行为的实质性意义:“如果你想要发表看法并引起他人注意,不必再苦苦地等待出版社或唱片公司来找你,只要涂鸦就可以了:只要你在墙上写了字,人们就一定会看到。涂鸦是‘自费出版’中最简单又最基本的形式。”(12页)我相信这是关于“涂鸦”的本质的最符合事实、最有逻辑性的表述:在墙上写字,有人看到,这就是出版!至于出版的目的,就是为了“出名”—— 就是让人知道自己的名字,尽管不是真实的名字。说起来,以涂鸦来“出名”,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作者引述了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在1974年讲述的观点:“这是在用名字打榜……现在,你的名字的排位已经超过了地铁制造商、交通运输管理局和城市管理局。”然后接着说,“个人的名字成为这种新兴的亚文化的焦点……如果说艺术反映了社会,那么在个人主义时代,有什么能比将个人的名字升华为一种艺术形式更合乎逻辑呢?对那些想让自己的名字成为像可口可乐、万宝路和耐克等全球性知名品牌的青少年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将它们刻满整个城市更振奋人心呢?涂鸦写手们模仿企业品牌的商标样式,把签名变成了艺术。”(16页)说得太对了,相比之下,那些想通过在资本主义体制中制造名气进而在市场上获利的艺术家显得太虚伪和太可怜了。
然后就是关于“涂鸦艺术”。“我们在查阅学术艺术史后发现,‘涂鸦艺术’(graffiti art) 作品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纽约东村艺术界的某些艺术家的作品,如让-米切尔·巴斯奎特、凯斯·哈林和肯尼·沙夫。”(10页)应该说,这只是在学术叙事语境中使用“涂鸦艺术”这个概念的一种方式,实际上指向的是建立在特定艺术家创作面貌上的作品分类。因此阿姆斯特朗接着就指出,“这些艺术家从不把自己称作涂鸦艺术家,而且真正的‘涂鸦写手’(graf writers)基本上也不会这样称呼自己。相反,那些非法涂画的人却常常称自己为“涂鸦写手”。一方面,‘graf’(‘graffiti’的缩写)一词意味着涂鸦创作者的创作内容不同于厕所墙上的乱涂乱画;另一方面,‘涂鸦写手’的称谓也表明这种文化有别于其他类型的艺术文化。此外,‘写手’一词的使用也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创作者们是用书写的方式将字母风格化,所以他们不认为自己是艺术家。”(11页)应该注意的是,从“涂鸦艺术”的概念马上涉及涂鸦行为者对自己身份的认同问题,他们不认为也不愿意称自己是艺术家,而只是“写手”,只用书写的字母风格化方式来解释似乎还不够。还应该从他们的动机、意图和目的来解释他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同。那就是作者在后面所说的,“签名客们不愿意自己被称为艺术家,他们想要成为破坏者”(86页)。说得很明确,涂鸦来自在墙上到处签名,就是要成为这个资本主义压迫体制下的“美好世界”的破坏者,用他们的行话来说就是要到处“轰炸”、不断“轰炸”,他们不是认为自己够不上“艺术家”的称号,而是根本就不屑。
最后是关于“街头艺术”(Street Art),阿姆斯特朗认为“这一术语的含义也不明确。从表面上看,它是一种‘艺术’,但却有着剪不断的反艺术渊源:藐视规则、颠覆类别、挑战法律”(11页)。这话首先就涉及什么是艺术的问题,说藐视、颠覆和挑战等行为就是反艺术,当然只是站在正统立场来而言。但是问题也很复杂,作者接着举出几位正统艺术家,说他们虽然从不认为自己是涂鸦艺术家,但他们的确与涂鸦的某些传统有明显的联系,这说明涂鸦的反艺术也与艺术有联系。但是无论如何,看来阿姆斯特朗还是要坚定维护“街头艺术”的“根正苗红”:“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虽然街头艺术是一门独立的艺术,有属于自己的创作材料与创作方式,但它的确是涂鸦的后代……街头艺术作为一种艺术运动,可以被视为对涂鸦犯罪化和当局严厉执法的回应,同时这一运动也标志着个体的行为从年少时的冲动胡闹转向了成熟的艺术创作。”(11页)这就是街头艺术的前世今生:来自涂鸦,当它发展为一种“艺术运动”的时候,有两个面向:继续回应和抵抗污名化与司法惩罚,同时让自己从冲动转向成熟。关于涂鸦和街头艺术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它们的动机不同:“街头艺术家倾向于致敬和美化他们身处的环境,而不是抨击或批判。”(12页)更具体来说,“街头艺术和涂鸦的区别在于,街头艺术希望吸引普通大众,而涂鸦却是一种更加高冷的、原生的、有力的反抗行为。涂鸦纯粹派对街头艺术不屑一顾,因为街头艺术被商品化了,而且很少在路灯杆上张贴贴画。这样的话,涂鸦最原始的能量和激情就都大打折扣了”(19页)。从受众对象的区分来看,被涂鸦真正吸引的的确是小众,而被商品化之后的原始能量与激情大减也是真的。对于艺术家来说,创作动机在有些语境中当然是重要的,比如在面对压迫性权力的时候,究竟美化还是批判,决定了艺术的真实价值。但是从接下来的论述来看,作者说的这种动机和受众的区别可能更多还只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本质上的,因为他接着指出在这两者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共性:一种紧迫感和一定程度上的反体制精神。这是作为“街头艺术”这个概念的根本性质,也正是因为这样,它会产生在艺术与个人命运这两方面的重要影响。对于个人来说,“一旦艺术家在创作中融入愤怒、悲痛和抗议等情绪,就会产生最具吸引力和最有价值的作品。街头艺术和涂鸦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例证。不过,这两种形式的艺术创作也很有可能会给你带来牢狱之灾,毁掉你的前程……由于巨大的风险和无尽的投入,所以最终能功成名就的人少之又少。另外,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街头艺术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完全由孩子发起的艺术运动,而且大多数知名的街头艺术英雄、偶像或者传奇人物的杰作都创作于他们的少年时期”(12页)。在不同的社会与历史语境中,少年或成为涂鸦写手向压迫性体制下的社会“轰炸”,或在艺考生大班里拼命内卷,真是不一样的“同学少年”。
初步了解了几个概念之后,涂鸦是否一种犯罪行为,恐怕是很多读者首先要问的。该书第一章的题目就是“犯罪成了艺术”,有意思的是,为什么不说“艺术成了犯罪”呢?到底是先有“犯罪”还是先有“艺术”?不管怎么说,涂鸦究竟首先是犯罪行为还是艺术行为,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在题目下面引述的是两位涂鸦写手的名言:“很久以前我就说过,涂鸦不是破坏行为,而是一种‘美好的’的犯罪。”(Bando、The Chrome Angelz,1986)说涂鸦不是破坏行为,这肯定不对,因为任何未经许可而在不属于自己的物品上的涂画行为的确就是一种破坏行为;说是“美好的”犯罪,未免也太诗意化了。无论如何,阿姆斯特朗还是要坚持对涂鸦的本质性认定和肯定,他认为“涂鸦本质上是一种反艺术运动,使破坏公物成为一种艺术形式。过多地关注涂鸦的审美价值是错误的……破坏行为本身要比创作出的签名或作品更重要”(16页)。涂鸦就是破坏,这甚至就是它的光荣,无需不承认。
事实上,恐怕大部分人对于在街道墙壁上的随意涂鸦都是不能接受的,无论是物权所有人还是社区居民,无论从环境美化还是管理者为此而要浪费纳税人的钱的角度来看。对此作者认为,“涂鸦到底是艺术还是犯罪行为?辩护者和批评者仅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但实际情况更为复杂。犯罪事实证实了作品的真实性”。复杂性与真实性是关于涂鸦艺术的更为重要的思考角度。阿姆斯特朗对西方世界的城市管理者处理涂鸦的心态作出这样的分析:“涂鸦揭示了批评者所畏惧的:失去控制、权力和价值。对当权者来说,涂鸦在视觉感受上是否有影响并不重要,但如果真的有影响,对他们也是有利的。他们关心的是,涂鸦是否会影响到意识形态。一旦涉及意识形态,就必定是零容忍。零容忍意味着当权者不需要纠结它是不是一种艺术,因为不管是涂鸦签名还是精心设计的模板画,是恶毒的涂鸦语言还是孩子们喜欢的卡通人物,它们都没有区别。任何未经允许的涂画都是犯罪行为,是对财物的蓄意破坏和刑事损坏。这是反对涂鸦的重要论据,也是唯一站得住脚的论点:只要损坏了财物就是违法行为。”(97-98页)这种分析在我们看来当然非常好理解,但不无疑虑和感到遗憾的是,作者没有举出一个具体案例来说明那些涂鸦在美国是如何被重判的。
说到底,在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是最关注涂鸦的,就是涂鸦写手和希望能在现场逮住他们的警察。涂鸦写手一边很内卷,为了显示出更多、更快、更大的难度和更惊人的传播,另一边要与警察斗智斗勇,因为这样才有最刺激的魅力。画笔或者喷漆罐从不离身,能在任何物体的表面进行创作,看着自己的签名符号从街道、社区、城市向全国和全世界传播扩散,看着这个签名如何成为被议论的对象、如何产生出神秘的故事,真是太令人兴奋了。孩子们不断猜测身边的谁竟然就是那位超级英雄,警察也很想知道他到底是谁,这种感觉也真是太酷了!随着法律对涂鸦行为的惩罚越来越严厉,以及警察安保系统的完善和闭路电视监控器的快速普及,涂鸦的手法也在变化,贴画、模板画和海报变得越来越普遍,因为它们能够确保涂鸦写手们在不被逮捕的情况下将涂鸦文化传播得更远、更广。于是就有了班克斯用模板画,“入侵者”(Invader)用瓷砖,谢泼德·费尔雷用贴画,“肥佬”(FALE)张贴海报,斯翁(Swoon)和“老鼠布莱克”( Blek le Rat) 用剪纸;万小姐(Miss Van)和雷福斯(Revs)也不再使用喷漆罐,取而代之的是油漆刷和滚筒刷。
这些新的手法并没有改变涂鸦的反抗性质,比如班克斯的《肖迪奇》(Shoreditch,2005年,模板和喷漆画,肖迪奇,伦敦)用白色油漆画了一条线用来代表可卡因,以模板法绘制的一个英国警察正跪在地上神情紧张地吸食着。这幅作品肯定令警察极为恼火,但是作者并没有因此惹上什么麻烦。谢泼德·费尔雷的《服从》(20世纪90年代,贴画)被批量生产,人们可以在世界各地的路灯杆上看到它们的身影。当数十张《服从》密密麻麻排在一起的时候,就像“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一样,不会让警察感到舒服,因为孩子们和许多大人都知道“服从”就是不服从,“好”就是不好……。
从涂鸦行为到涂鸦艺术作品再到街头艺术,就这样从非法、匿名、抗争发展到既有非法也有合法、既是匿名又是扬名的城市艺术阶段。在这时,“有些艺术家一边在街头进行非法创作,一边在画廊举办展览,拍卖自己的作品。合法和非法的创作方式、街头涂鸦和工作室创作,它们如同艺术的阴阳两面,两者的斗争既微妙又复杂,永不停歇。……有些人因此进了监狱,而有些人则去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24页)。
可以说,涂鸦艺术就是都市文化中的杂草。英国博物学家理查德·梅比(Richard Mabey)认为对于什么是“杂草”(weed)难以给出明确的植物学定义,因此只给出一个他认为最为人所熟知也最简单的定义:“出现在错误地点的植物。”(梅比《杂草的故事》,陈曦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7页)好一个“出现在错误地点”,这不就是治安警察要逮捕涂鸦写手的基本理由吗?出现于“错误地点”的涂鸦所表达的是一种野性的生存意志,那些涂鸦写手就像杂草一样在都市间流离颠沛、在社区中自生自灭,因此他们的街头政治学就是藐视体制、反抗秩序、戏弄一心想逮捕他们的警察。也正像梅比对杂草的那种敏感认识所描绘的,“杂草的生态形象和文化形象总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它们是面熟的邻居,非法定居的植物居民,一种有生命的涂鸦——无礼粗鲁,通晓城市的生存技巧,永远比开发商和寻衅于它们的人领先一步”(276页)。说杂草是“有生命的涂鸦”当然很准确,反过来说涂鸦也正是有生命的杂草。最后那句话更是很精彩,涂鸦也一样,永远比西方世界的开发商和警察更早认识到街头的存在。接下来,梅比认为杂草对于我们的意义是:“它们是边界的打破者,无归属的少数派,它们提醒着我们,生活不可能那样整洁光鲜、一尘不染。它们能让我们再次学会如何在自然的边界上生存。”(282页)的确,每当我们在街头看到不管是什么风格的涂鸦,总会感到有一种鼓舞的力量。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保持天真、纯粹的涂鸦精神,警惕所有贴在涂鸦身上的标签,尤其是那些骨子里散发着媚俗气息的伪反抗标签。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虽然街头艺术已经越来越被融入艺术市场和都市文化,但是它的初心和野性尚存。在“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中,涂鸦写手的身影仍然闪动在地铁月台与车厢;在广场上仍然可以看到涂鸦文字,学生们举起的横幅标语 “Were not a loan”(“我们不是贷款”)更是一派当年涂鸦抗争的口吻。因此,作者在全书最后用了一个小标题:“街头艺术万岁”,读到这里我真的是被深深触动了。阿姆斯特朗说,尽管涂鸦签名和涂鸦绘画已经被社会大众接受,“但公众渴望的公共空间仍需去争取和占领,这与涂鸦占领空间的使命是一致的”(173-174页)。